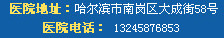近日,新冠疫情在河北省境内复燃。河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李琦指出,此次疫情在石家庄地区主要分部在农村地区,以农民感染为主,占所有感染者70.07%。与此同时,“此次疫情蔓延系天主教会活动导致”的传言亦在网络不尽而走。
为此,河北省天主教爱国会与天主教石家庄教区特别公开发言澄清疫情与教会活动无关,感染者仅有1人为天主教友。此外网传的石家庄市蒿城区公布治理地下天主教会的通知亦发生在疫情之前。
显然,基督宗教与此次疫情传播并无直接关系。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基督宗教在中国农村确实存在一定影响。为什么拥有本土信仰传统的中国农村,会成为基督宗教的发展土壤呢?
基督宗教扎根农村早已有之
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对国内基督宗教的第一印象似乎是坐落在各大城市内漂亮的大教堂。但其实,中国基督宗教——无论是基督新教还是天主教——信仰人口的主力还在农村。年公布的《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基督徒总数的80%分部在农村。中国人民大学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统计,基督宗教信众中拥有农村户口的比例分别为64.3%。若加上曾经拥有农村户口的人数,则比例更高。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农村一直是基督宗教传播的重要方向。天主教会明末即正式传入中国,此间经历康乾时期因为“礼仪之争”有所中断,后着《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的签订后重新开放。
当时传教士即发现相比城市,农村才是中国社会之主体,遂有不少传教士进入农村,不仅兴建教堂,更购置田产后以低价租给佃户种植,以吸引更多农民信教,逐渐形成教友村落。这也导致了中国各地都存在历史悠久的天主教村,有些至今仍然存在。
进入20世纪,教会从庚子之乱后快速复兴,信众人数从年的74万快速增加到年的万人,其中大多数依旧来自农村。
新教进入中国较晚,要到鸦片战争以后才有传教士正式进入中国大陆。而农村传教则是20世纪以后方才兴起。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园艺学专业的传教士高鲁甫(GeorgeGroff)来华进行农业传教。到年代,根据当时金陵神学院乡村教会专家毕范宇的说法,当时全国多间教会堂点中三分之二在乡村地区。此时新教已经成为当时农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持续到年方才停止。
民国时期的农村基督新教传教士与信众(资料图)
当代基督宗教在中国农村的发展根源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重新落实,基督宗教在中国也迎来了复兴。农村教会在新时期再次成为了教会发展的主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城乡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差距明显。农村人口收入普遍不高,社会保障水平低下,导致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机会和患病后获得足够的医疗资源的机会都偏低。不少关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教会的研究都指出,中国农村教会信徒构成有“三多一少”的特点,即老人多、妇女多、病人多、受过教育的人少。这些人群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都极易陷入匮乏状态,而教会某种程度上则能缓解这种匮乏,因而迅速发展壮大。
不少教会能够对农村孤寡老人和病人提供一定的经济救济,生活上的照料,提供了一个与人群接触免于孤独的场所,自然也提供了精神和心理上的慰藉。有些教会还会特别强调“医治”能力,因此吸引了一些身患重病无法治疗的病患信徒。然而,这也导致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农村教会容易滋生狂热、反智现象,甚至出现邪教。
此外,基督教得以在中国农村复兴,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村“信仰生态失衡”。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本是传统信仰和价值体系的中心。无论是儒家宗族体系还是民间宗教的鬼神信仰体系,在农村都是延续的最为完整。然而清末开始的社会变革,使得农村士绅宗族结构松动。建国后的剧烈政治运动,也对这些传统信仰体系的根基产生动摇。改革开放后,重新获得合法活动资格的基督宗教得以迅速填补这种“信仰真空”,在农村信仰生态系统中茁壮成长。
年代的农村天主教聚会(资料图)
第三,天主教教友村得以长期保存,得益于近百年来天主教尤为注意信仰的本土化。尽管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传统礼俗采用了宽容策略,康乾时期的“礼仪之争”导火索,就是当时耶稣会以外的传教修会坚持中国信徒不得参与传统的祭祖和祭孔礼俗,并要求罗马教廷正式颁布了禁令,激起了清廷与民间的一致反感。
有鉴于此,清末重回中国的天主教会重拾灵活方式,允许中国信徒参与传统礼俗。年,教廷传信部颁布《中国礼仪敕令》(Plane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wh/5732.html